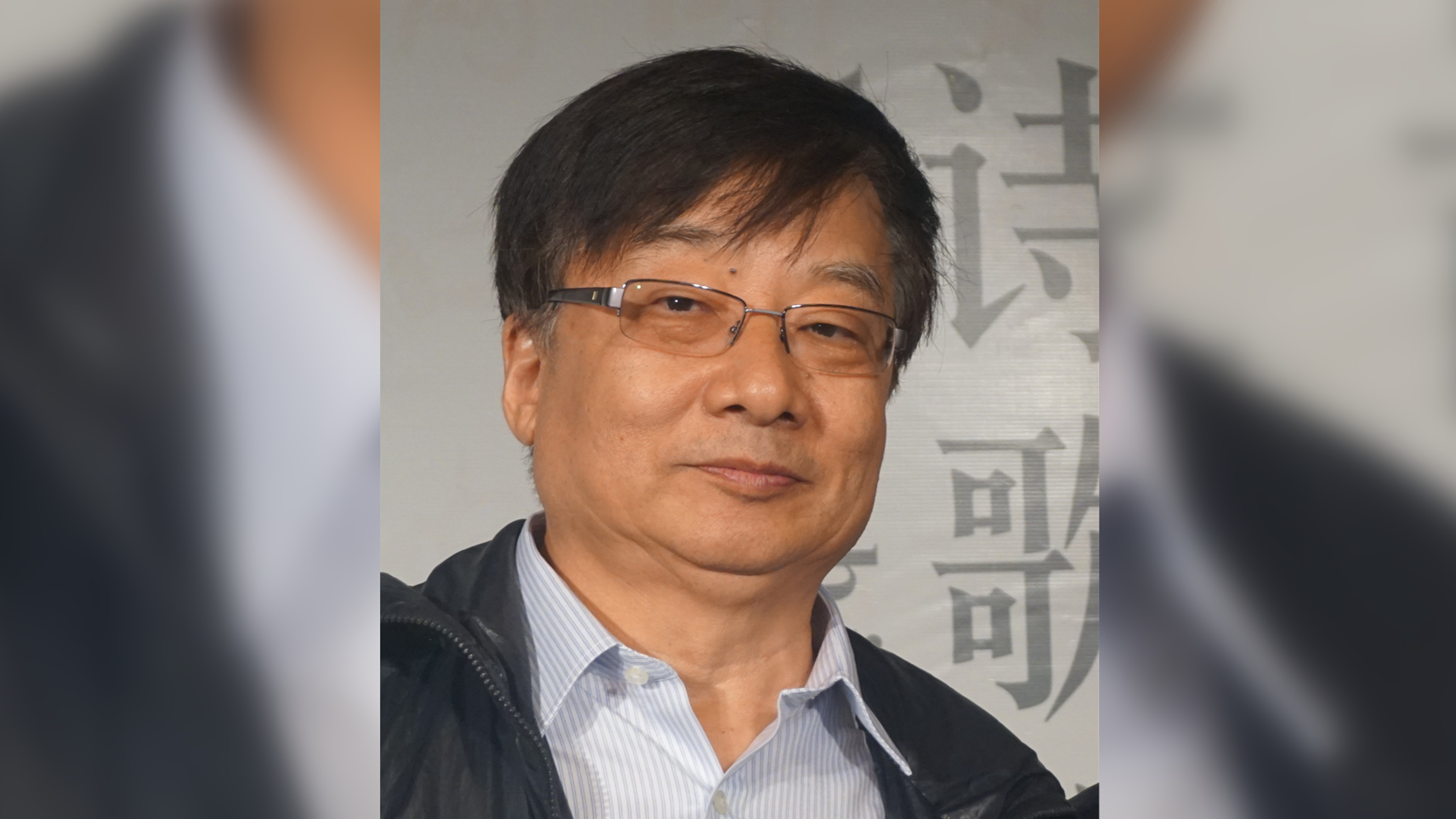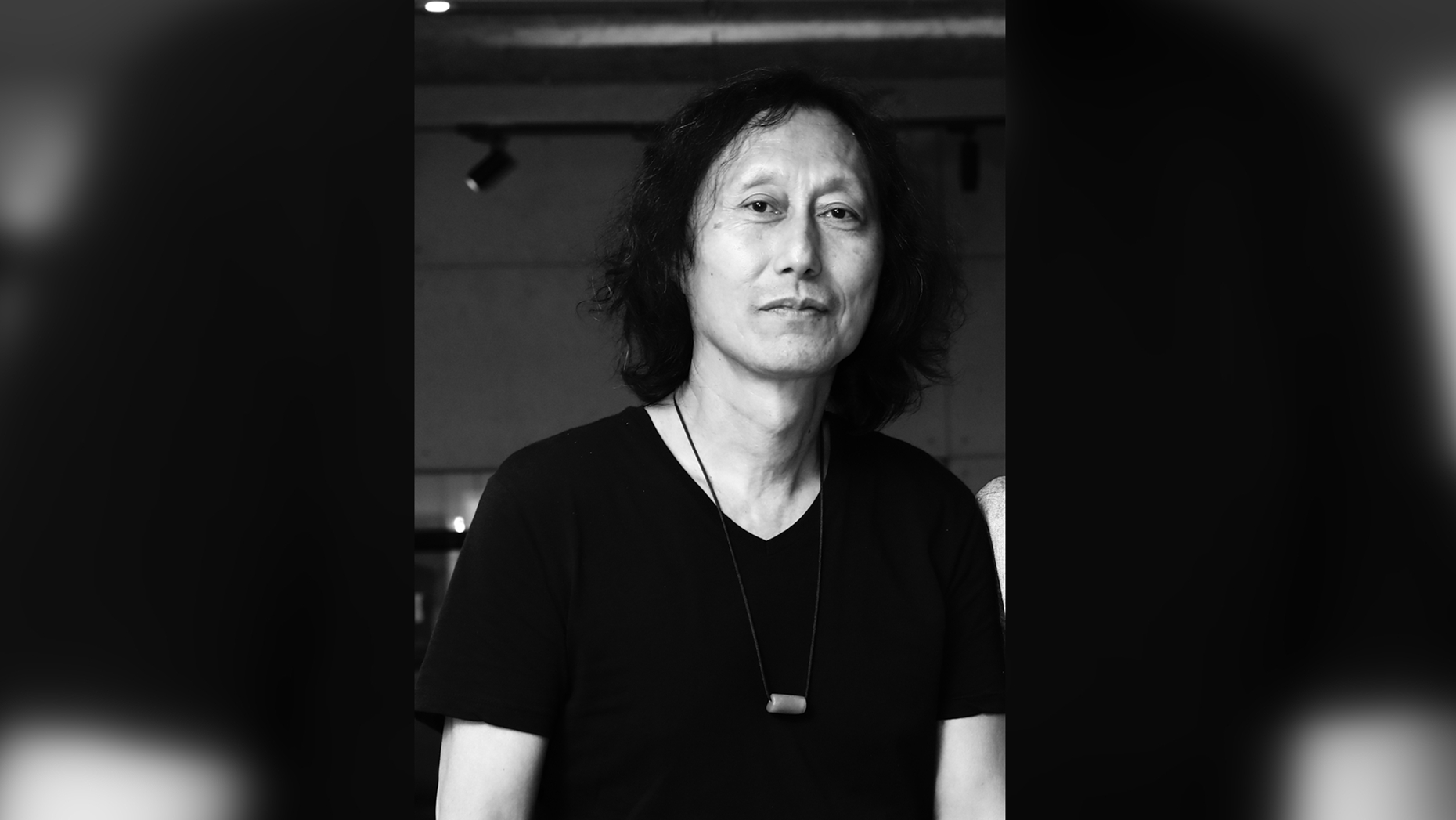
荊歌
對於家庭陳設,我一向都是喜歡中西合璧的,也即所謂混搭。明清的古花瓶,和西洋的琺瑯鎏金時鐘一起擺放在法國古董胡桃木雕花邊櫃上,有著特別和諧的美感。康熙的雙龍戲珠紋青花瓷盤,和購於馬德里的古典油畫懸掛於同一面牆上,非但沒有絲毫的違和,反而顯得別有情趣。
我這樣有著亦中亦西喜好的人,來到廣東江門開平自力村,特別是走進「銘石樓」,室內的景象真是讓我感到意外又驚喜。這座建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房子,它優雅時尚的品位和氣息,讓我不敢相信它竟是與我隔著百年時光的,它讓我頓時有了夢幻的感覺。更為不真實的是,這樣的樓宇在自力村,在開平,並非孤零零的一座,它們神奇地錯落在山水田野之間,仿佛海市蜃樓,又給人以置身異鄉的錯覺。
曾經是什麼樣的人,在這裏建造了如此豪華摩登的房子?屋子裏的一切,其年代和地域的特徵完全恍惚模糊了。難道這是一個為拍攝電影而建起的基地嗎?還是我一不小心走進了一部荷里活的老電影,或者翻開了杜拉斯的東方小說?
一切都是如此靜悄悄地擺放在這裏,雕花繁複的廣作椅子,花紋淡雅的布面沙發,包漿油亮的地磚,神態嫻靜的老照片,玻璃略有斑駁的梳妝枱,花朵一樣盛開的留聲機,還有依舊從容地來回擺動著的落地自鳴鐘。仿佛主人還在書房閱讀,也許是在躺椅上小憩。又也許,那精心布置了這些的主人,早已經穿過時代之牆,去了遙遠的地方,把這立體的一切,變成了平面,變成了可以鑲進相框的照片。那是一個遠去的時代,又是那麼的近,近在眼前,近得可以讓我聽到房子主人的呼吸,似乎能聽到留聲機里傳出來周旋或李香君的歌。趙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仿佛不是為一個人而寫,而是唱給一個時代的歌。那個一直都只是活在想像里的時代,由模糊而清晰,清晰到我們完全可以拎包入住,可以在這樣的房間裏坦然舒適地住下來,像從前的主人一樣有滋有味地生活。在嘀嗒嘀嗒的古老鐘聲里,庸常曾經的庸常,悲歡他們的悲歡。
那個時代原來離我們很近,其實離我們也很遠。在曾經貧窮落後的南國,在還是相當封閉的年代,有一些人,為了更好的生活,漂洋過海,去尋找他們夢想中的「金山」。他們經歷了怎樣的海上風浪,遍嘗了怎樣的酸甜苦辣,人們也許並不知道。村上的人們,看到的是他們真的抬著金山回來了。那碩大的皮箱,裝著滿滿的金銀。這樣的皮箱,就被人們命名為了「金山箱」。他們還運回了奇異的鋼鐵和玻璃,更奇異的物件,以及他們衣錦還鄉的榮耀和思鄉的心。他們要用他們打拼到的財富,回家鄉構建起他們的樓宇,那是他們艷羨了多少年的,夢想了多少年的。那曾經是鏡中之像,隔岸的風景,他們卻把它變成了可以拿在手裏扛在肩上的實實在在的東西。他們要把它們帶回故里,讓它們在自己的家園裏矗立起來,成為他們的豐碑。
他們不懂建築,也不會設計,他們就把帶回來的明信片給家鄉的工匠作為藍本。明信片上恢弘綺麗的建築,讓家鄉的土木匠泥瓦工看得目瞪口呆。這些聰明智慧的鄉親,就憑着那些個蓋著郵戳的洋畫,比劃,琢磨,商量,終於讓一座座漂亮氣派而又有些奇異的大樓,在鄉村的荷花塘邊古榕樹旁巍峨聳立。
據說,在開平縣,有幾千座這樣的碉樓和屋舍。那真是一個沸騰的年代!世世代代的嶺南鄉親,突然間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為自己營造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們用心建造了它,也用心守護著它。他們為這些樓宇設置了周密的防禦機關。他們不能讓自己闖蕩天涯獲得的財富被搶劫掠奪,他們要捍衛他們用勇氣、智慧和心血換來的富足生活。
原來,在廣東這塊改革開放的熱土,曾經有過一段遙遠的謠曲,竟然能夠與後來的壯美旋律神奇地呼應。一百年前那幾朵浪花雖小,卻與今日改革開放之大潮如此地合拍,真是讓人無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