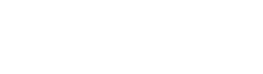終于站在了興凱湖畔。
記得還是30多年前在哈爾濱讀大學時,班上有一群來自上海的知青,在他們嘰嘰喳喳的交談中,經常會蹦出“密山”、“八一農大”和“興凱湖農場”幾個字。想象中,興凱湖是個遙遠而又荒僻的去處,要不咋會讓這些皮白肉嫩的城里人去那兒“接受再教育”呢?早他們10年,那幾個大名鼎鼎的文化人——丁玲、艾青、聶紺弩、丁聰、吳祖光不也是在那兒接受“勞動改造”嗎?
想象歸想象,興凱湖有苦寒,也有詩意。在赫哲語中,“興凱”的意思是水從高處往低處流,在滿語里,“興凱”的意思是水耗子,由此可見興凱湖的原生態特征。有意思的是,歷史上,興凱湖曾經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北琴海,因為它地處“胡天北地”,形狀又極像一種中國古典彈撥樂器——月琴,在我看來,這個名字的詩意不亞于希臘半島旁邊那個充滿浪漫情調的愛琴海。

濕潤滋生萬物,濕潤孕育文明。考古證明,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期,興凱湖畔就是肅慎人的領地,肅慎是女真和滿族人的祖先,也是北方最早的先民。他們在遼闊無邊的興凱湖上捕魚,在湖畔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打獵,在沃野千里的黑土地上耕作,創造了我國北方早期的農耕漁獵文明。
漫步在草木繁盛的湖崗上,不經意間撞見一尊高大的雕像,根據我行前的功課判斷,這應當是新開流文化遺址。果不其然,走進一看,雕像的基座上寫着“大湖文明之光·肅慎人”。這名肅慎人右手持一柄長矛,左肩上站着一只魚鷹,腰間系着捕獲的獵物,目光炯炯,神情勇武。不難想象,那時候的興凱湖畔就是北方的“魚米之鄉”,肅慎先民們過的是“棒打麅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的生活。
與國內其他大湖不同,興凱湖是個界湖,橫跨中國和俄羅斯,其中三分之二歸俄羅斯,三分之一歸中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還是那個軟弱無能的清政府,本來歷史上興凱湖一直是中國的領土,可1860年的一紙條約,一片完整的水域就被切了西瓜。
清朝初年,大批滿清人隨軍入關,關內的漢人又被禁止出關,作為“龍脈之地”,興凱湖一带被封禁起來,長達200余年。這就給一向覬覦鄰國土地的北極熊以可乘之機,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俄國人乘虛而入,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將興凱湖自松阿察河口至白棱河口以南的水域割讓給了俄國,自此,興凱湖由內湖變成了界湖。
站在興凱湖畔,遙望煙波浩渺的湖面,讓人對歷史生出無限感慨。

新開流文化遺址
親臨其境才知道,興凱湖有大小之分。在月琴形的湖面頂部,有一道東西走向、寬數十米、長90公里的“湖崗”。湖崗筆直,如同人工築壩,將湖面分為兩部分,湖崗以北為小興凱湖,湖崗以南為大興凱湖。讓人驚奇的是,一崗之隔,竟然兩個世界。登上那座高高的帆船造型觀景台,可見大興凱湖波濤拍岸,橫無際涯,大氣磅礴,恍惚中,讓人以為是來到了海邊;小興凱湖畔沼澤密布,湖面波瀾不興,帆影點點,溫柔恬靜。

煙波浩渺的大興凱湖
同一片湖水,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大的差異?我在《地理.中國》節目中看到,有學者前往考證,得出的結論是,導致大小興凱湖景觀差異的原因就在于那道高高的湖崗,它像一道山梁,減弱了東南方向吹過來的太平洋海風。而這道湖崗則是由于數萬年的湖底水流回旋,淤積出來的一道水下堤壩,隨着湖水的退縮,這道堤壩慢慢露出水面,形成了今天的湖崗。

溫柔恬靜的小興凱湖
10集電視紀錄片《龍之江》稱:“被完達山與烏蘇里江環抱的興凱湖魚豐水美”。在當壁鎮湖邊的一戶漁民家里,我們有機會近距離看到了興凱湖大白魚。這種魚看上去體型修長,色白如銀。漁民告訴我們,大白魚與烏蘇里江的大馬哈魚、綏芬河的灘頭魚被稱為“邊塞三珍”,這種魚味道鮮美,原因是它只吃湖里的小魚小蝦。漁民說,大白魚主要產于大興凱湖,現在咱們這邊野生的大白魚已經很少了,主要靠網箱養殖。旅游旺季時,大白魚的價格是200元一斤,現在是淡季,但也要120元一斤。
出乎意料又讓人驚喜的是,大興凱湖畔有一片面積不算小的沙灘,這讓我這個喜歡戶外行走的人着實過了一把與沙水親近的癮。水清沙細,微波蕩漾,脫掉鞋子,站在水邊,任由浪花陣陣拂來,輕輕拍打腳面,然後率性地在沙灘上走幾個來回,讓腳掌腳趾紮紮實實地深入細軟的沙粒中,體驗肌膚與沙粒摩擦的感覺。這是一種人與大自然的無縫接觸,酥酥的、癢癢的、微微有一些刺激,一種足底按摩體驗不到的感覺。
大興凱湖產魚,小興凱湖產鳥。我手頭有一本2008年第10期的《中國國家地理》雜志,里面有一篇文章,名字叫“春季到東北來看鳥”。作者認為,塔頭甸子遍布的興凱湖濕地是候鳥遷徙的重要加油站。每年四五月間,來自東南沿海、長江中下游、渤海灣等越冬地的候鳥都要在此停歇聚集。據說最多的時候一天可達17萬只之多。那當是一個草木競發、野花開放、魚躍水面、鷗鳥翔集的場景。如今,人們在小興凱湖畔建起了觀鳥平台,還有深入濕地的觀鳥棧道和觀鳥游船,可以近距離與這些珍稀鳥類接觸。
在眾多的鳥類中,我對丹頂鶴情有獨鐘,我在北方的松嫩平原看過度夏的丹頂鶴,在南方的江蘇鹽城看過越冬的丹頂鶴。在千里迢迢的遷徙之路上,興凱湖是它們的重要驛站,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雖然已近初秋,錯過了觀鳥的最佳時節,但走在闃無人跡的湖畔仍不時能見到有三三兩兩的水鳥從湖面掠過,讓人興奮不已。

興凱湖畔,水稻即將收割
秋水長天,涼風陣陣,告別興凱湖,我們一路向北,穿行在即將收割的金黃色稻田中,伴着藍天白云,向三江平原腹地駛去……
(作者:劉文軍,黑龍江籍,現居北京,QQ:267701833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