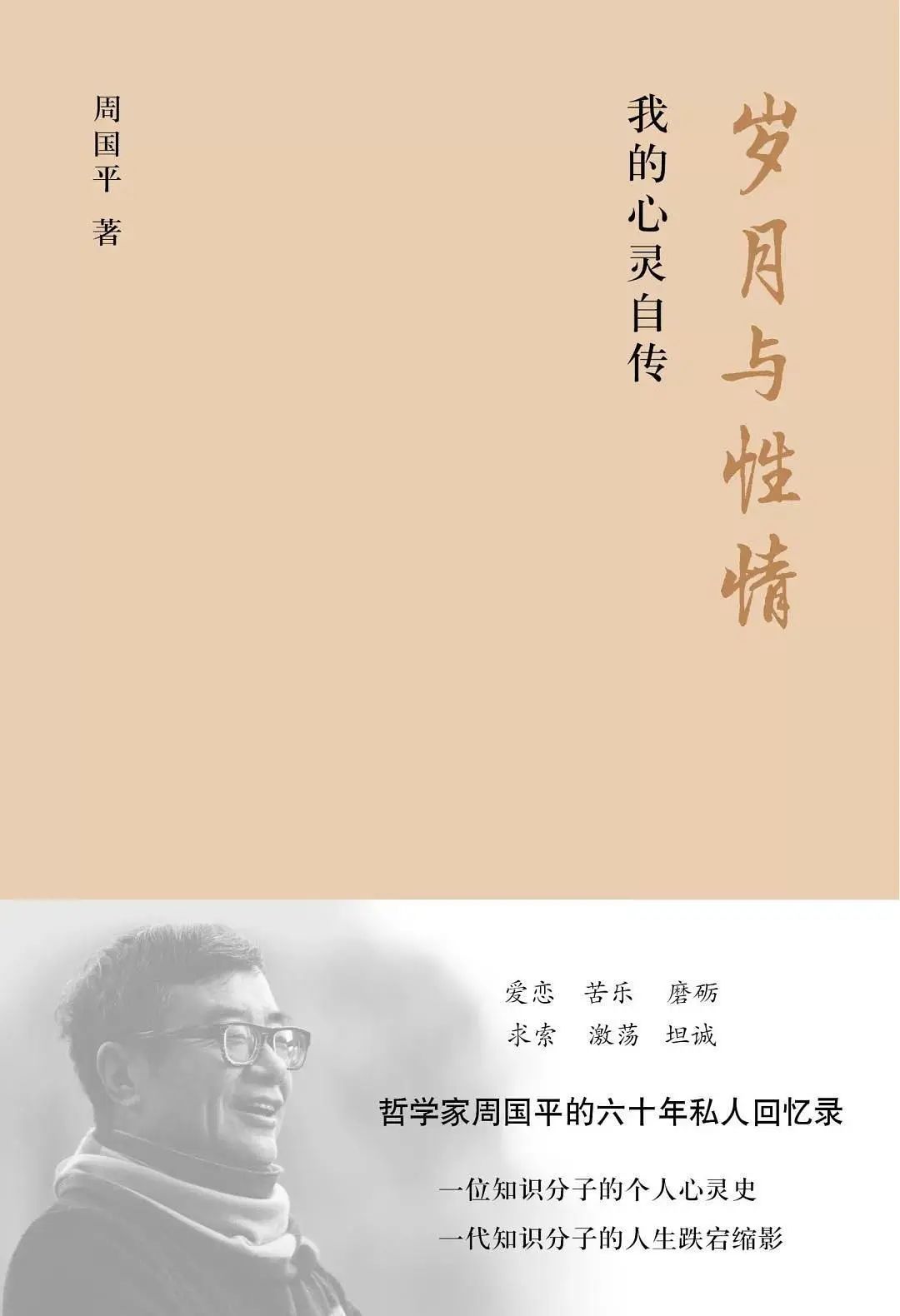我寫過一篇短文,大意是說:我跟在一個灰色的人影背後走人生的路,從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轉過臉來,臉上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以為這個世界也是痛苦的。現在,這個人影消失了,但我沒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反而覺得世界空了。
——周國平

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車從上海出發開往北京。車廂里擁擠悶熱,列車又開開停停,使得人們很不耐煩,經常有人唉聲歎氣。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個少年始終很平靜,一張未脫稚氣的臉,面容有些消瘦,臉色有些蒼白,戴着一副650度的眼鏡。正是在這個少年身上藏着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碼。我不知道未來將是怎樣的,但卻意識到這次遠行是一個轉折點,童年歲月已經永遠留在我的身後。
到達學校後,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領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學系的宿舍在38樓,我的寢室是120室。四張雙層床,四張簡陋的書桌,住八個人,擠得滿滿的。到校當天,有消息靈通的同學對我說,郭沫若的兒子在我們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學校,這沒有什麼。見到郭世英是在兩天後,各班分組討論系副主任的入學教育報告。人們擠挨着坐在寢室里,一個接一個發言。郭世英也發言了。
他坐在雙層床的下鋪,微低着頭,長發下垂,眼睛凝視着地面。聲音深沉而悅耳,話音很低,有時幾乎聽不清,仿佛不是在發言,而是一邊思考一邊自語。他說的大意是,從高三開始,他對哲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讀了許多書。哲學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種理論是不是真理,必須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來檢驗,對馬克思主義也應如此。
當時我並不真正理解他的話,我相信別人更是如此。在座的人中還沒有人想到要自己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因而對他的問題和苦惱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為如此,我格外鮮明地感覺到,眼前的這個人屬于一種我未嘗見過的人的類型,其特征是對于思想的認真和誠實,既不願盲從,也不願自欺欺人。這是一個真誠的人,一個精神性的人。
他的外表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個兒,體格勻稱結實,一張輪廓分明極具個性的臉,很像一張照片中的青年馬雅可夫斯基,經常穿一件中式對襟布褂,風度既朴素又與眾不同。當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質,除了思想上的真誠之外,他又是一個極善良的人,對朋友一片赤忱,熱情奔放,並且富有幽默感,頑皮而善于說俏皮話。

後來通過交談,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經歷。他中學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學校一零一中學。在學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學生、模范共青團員,被譽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級不同班有兩個學生,一個是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另一個是將門之子孫經武,因為思想反動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會上主將的角色。到快畢業時,他開始反省自己,進而否定了自己的過去,從此與這兩人有了密切來往。離開一零一中後,他進外交學院上學,然後轉學到了北大。
北大雖然開了西方哲學史課程,但是一則教科書貫徹階級觀點,內容簡單片面,二則課程沒有學完,因參加四清而中止了。不過,我還是讀了幾本原著,有休謨、馬赫、羅素等,並且邊讀邊記錄我的理解和思考。
當時有少量西方現代派作品被翻譯過來,用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級別的干部才有資格買,世英常常带到學校里來。我也蹭讀了幾本,記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荒誕派劇本《等待戈多》、《椅子》。愛倫堡也是世英喜歡的作家,由于被視為修正主義者,其後期作品也是內部發行的,世英當時已讀了《人,歲月,生活》。在同一時段,世英還迷上了尼采,經常對我談起,不過我在他的案頭只看見一本蕭贛譯的《紮拉圖士特拉如是說》,因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沒有讀下去。

有一回,他拿給我一本內部資料,上面有薩特的文章,建議我讀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義。大約是受孫經武的影響,在尼采之後,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我曾向他借這本書,他沒有答應,笑着說:“你也想讀?早一點了吧!”通過自己閱讀,也通過世英的談論,我對現代西方文學和哲學有了零星模糊的了解。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這已經很不容易,如果沒有世英,我也接觸不到。
我是抱着做學問的理想進北大的,進來後發現,北大並不是一個做學問的地方。不過,在世英影響下,我的初衷已經悄悄發生了改變。學問不是第一位的,生活本身高于學問,做一個有豐富內心世界的人比做一個學問家更有意義。
世英經常說,生活的意義在于內心的充實。這句話也成了我的座右銘。他自身就是我的一個榜樣,雖然在同學們眼中,他是一個走入了歧途的人,但我相信他比我所見過的任何人都活得真實。他本是一個孩子般赤誠的人,只因對于精神事物過于執著,才常常陷入痛苦之中。我心想,我寧願像他那樣痛苦,也不願像別人那樣滿足,因為他的痛苦其實是充實,別人的滿足其實是空虛。
有天午睡時,我聽見他在窗外叫我,便翻窗出去。他旁邊站着張鶴慈,他們想去喝酒,但沒有錢了,向我借錢,還要用一下我的學生證去舊書店賣書。他們三人經常去飯店喝酒,在半醉中寫作。
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們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另類。他們的行為,一半是對現實的反叛,一半是對西方藝術家的模仿,我估計主要是在模仿《人,歲月,生活》所描寫的洛東達酒吧里的榜樣。使我越來越擔心的是,世英的情緒這樣放任下去,與現行制度的沖突日趨激烈,不知會走向一個怎樣悲慘的結局。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學僅兩年,農村四清兩年,文革又兩年。在這六年中,我與世英有兩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學一年級,另一是直到他去世。當我回顧我的北大歲月時,與世英的交往無疑是其中最難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說,我從這一交往中學到的東西,遠比在哲學系全部課程所學更多,當然也更本質。如果沒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憑借悟性走上後來的路,不過這條路上的風景會遜色得多。對于我來說,在一定的意義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學時代。
本文節選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