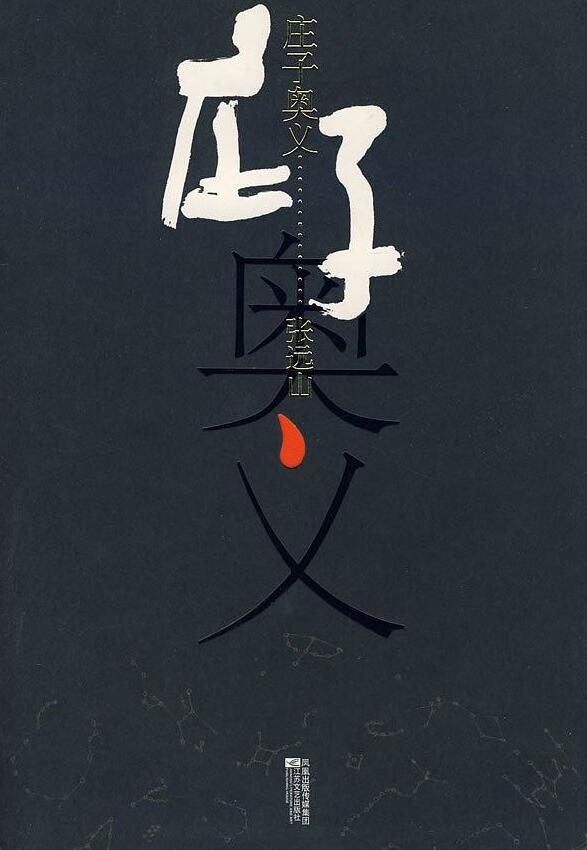
作者:龍建人
多年前觀看魯洪生先生講授《周易》的視頻,獲益良多。魯先生講授過程中,特意舉了《莊子·養生主》中著名的寓言"庖丁解牛",以證《周易》 "相似關系引發類比聯想"的思想。該寓言中,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技藝極為精熟,其行"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魯先生指出,是篇的隱含意義為庖丁是在"說明自己不受政治干擾,快樂地逍遙地生存",而"莊子本來講的是實現逍遙的方法"。這一見解不同于之前常見的"認識規律,掌握規律,精益求精"的俗論,猶如漆靜的夜空中一粒彗星倏然閃過,瞬間拉出一縷亮眼的光芒。直覺告訴我,魯先生的見解較那些俗論,其深刻性不止以道里計,且貼近莊子的本義。遺憾的是,整個《周易》系列的講座僅有此處提及對《莊子》的解讀,在網上搜索也未能找到他解《莊》專門著述,我只能與《莊子》一書的真義失之交臂。直到前幾年,遇上了張遠山先生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奧義》一書,當然,彼時該書尚以《莊子奧義》名。
在我褊狹的視野和閱讀中,除了艱澀的德國古典哲學著作外,還有兩位大哲的作品我未能真正進入,一位是尼采,一位就是莊子。二人雖然身處的時代和環境頗有異同,然而其作品卻有着一些共同點:以文學的修辭和形態呈現鋒銳的思想。尼采以詩性十足的格言體批判蘇格拉底以降的形而上學家和彼時的德國文化,修辭考究,詩意盎然;莊子則刻意"支離其言、晦藏其旨"地發揮自己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以寓言的形式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僅就字面而言,二者整體上皆是易于閱讀的,但二者又都像卡夫卡的"城堡",易近而難進。莊子親撰的"內七篇"中,寓言一個接着一個,讀者往往會深陷以致迷失于其瑰麗的想象中。作為一位影響深遠的大哲,莊子必然不會為寓言而寓言,必然有所寄寓,他筆下的故事僅僅是他所欲表達的思想的外衣,是一套等待破解的謎面。欲進入莊子的世界,除了找到破解之法外別無他法。讀者只有找到對路的密碼,才有可能由表及里地把握莊子的思想。在我看來,《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奧義》(下稱《莊子奧義》)就是一部破解了莊子思想密碼的書。如果說,魯洪生先生不經意間對"庖丁解牛"的解讀是暗夜中的一縷光亮,那麼,《莊子奧義》就是一支由無數縷光亮聚合的火炬。
作者自云:"初讀《莊子》,竟然不懂。從此以後,我讀一切書,都是為了讀懂《莊子》。"(《作者序言》)初讀不懂,應該是所有讀《莊》者的共同感受,于是作者找來了百種以上的《莊子》版本,反復閱讀,終于完成了對《莊子》一書的破解。在作者看來,《莊子》之所以難以進入,原因有二:其一,《莊子》的寫作者為了某些隱秘的目的,他既要批判當時的社會,又刻意將自己的思想隱藏,正所謂"支離其言,晦藏其旨"。由此,莊子創造自己的特殊寫作方法,以"寓言、重言,卮言"的方式進行。"寓言",即是寄寓了深刻意義的故事。"重言",重讀作chong,即重復之言。"卮言",其意有三:首先,"卮"借為"至","卮言"即"至言";其次,"卮"為酒器,空時上仰,滿則傾空,隱喻莊子"其意述滿之後,又予以傾空至無";再次,"卮"借為"支",即支離。在《莊子》一書中,本應點明寓言寓義的語言破碎地散離各處。其二,就是西晉儒生郭象對《莊子》一書的系統篡改和反注。郭象為學宗儒術,以儒學之理對《莊子》進行注解。有違儒學義理之處,則削足適履,對《莊子》文本恣意妄改。郭注本《莊子》影響甚大,一千多年的時間足以積非成是。當然,郭象以降,並非無人窺破《莊子》一書的奧秘,但僅有李白、蘇東坡、劉基、金聖歎等數人而已。
《莊子奧義》為作者耗費數十年心血研讀《莊子》的成果之一(此外尚有《莊子復原本》《莊子傳》)。在人生如此漫長的時段中,作者搜集了百余個《莊子》的版本,吸收了多代學人的成果,逐一訂正了慘遭郭象篡注的《莊子》文本,厘正訛誤,正本清源;與此同時,作者又以戰國時代遺留的史料為依據,訂正了包括《史記》在內的諸多史書中存在戰國錯誤年表,為莊子本人所生活的時代建立起了時間和空間上的坐標,還原了《莊子》一書的寫作語境。研究莊子,必然要清楚其所處的時代大勢、所處的國家、交友及思想源流。其身處的時空坐標的建立,對研究《莊子》文本必然大有禆益,因為以該坐標為出發點,可以清楚地知道《莊子》諸篇什中其提及的論戰對象的生平、思想源流等,反過來又有益于理解《莊子》的文本。該書以詳細解讀《莊子》"內七篇"為目標,冠首有名家序,作者前記、自序,計四篇;介紹戰國大勢、莊子生平及郭象注《莊子》及對《莊子》的增刪的緒論,計二篇;對《逍遙游》《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师》《應帝王》"內七篇"的破譯,計七篇;余論為作者對莊學思想深入研究之後發揮,計三篇;跋一篇。在主體部分的七篇中,主要就是對其原文的逐字逐句的解讀,並從中晰出了理解《莊子》一書的關鍵概念。
《逍遙游》為"內七篇"之首,亦是《莊子》一著的大綱,起提提綱挈領作用。莊子以其天馬行空的強大想象力,從"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開始講起,以"樗"的寓言結束。鯤鵬、蜩鳩,朝菌、蟪蛄,冥靈、大椿等關鍵形象穿插其中,這是莊子特有的思維和表達方式。這些能指有何所指意義呢?作者認為,莊子以這些形象來編織寓言,是要講清楚"莊學四境"的相關問題:蜩鳩、蟪蛄等,代表莊學的"小知"之境,境界高于朝菌代表的"無知",而鯤鵬、冥靈,則代表着莊學中的"大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高于"小知"之境,而大椿、"藐姑射神人"則代表着"至知"。由是,"無知→小知→大知→至知"這樣的位階排列,就是《逍遙游》所確定的"莊學四境"。茲四境就是由束縛到逍遙不斷上升的序列,也是從有待、處處受縛到達"自由"的序列。故而,作者將《逍遙游》理解為"蘊涵四境的'自由'論"。以"莊學四境"為坐標點,再回過頭去審視《逍遙游》原文,其中一個接着一個寓言就易于理解了,讀者也能抵達該文的核心,對來源于文本的一些問題也會有明確判斷。譬如:大鵬"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它是"自由逍遙"的麼?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大鵬在莊學四境中屬于"大知",它離"至知"尚有距離,依然有待。達至"逍遙"之境後又如何呢?作者按照自己整理的文獻成果,認為莊子的答案是"無極之外復無極",而不是郭象所注的"物各有極"。
"物各有極",實際上是否認了自然之"道"對世間萬物的統攝,而肯定了世間萬物的高低等級性。"內七篇"的次篇《齊物論》文辭古奧,是整部《莊子》中最難理解的篇章。在作者看來,該篇核心正是"萬物齊一"的"平等",也就是從"道"的角度來看,世間萬物皆"平等"。這是作者所提出的"道極視點",與郭象之流所秉有的肯定等級性、"物各有極"的"人間視點"相對。在莊子看來,"物德之質與道同質,因而萬物齊一,萬物平等",這是實現《應帝王》篇中提出的"天人合一""至人"論的基礎。在治《莊》史上,對于這些關鍵問題,諸多學者語焉不詳,有些讀解又左支右絀,前後矛盾,造成了邏輯上不能自洽,反而使得對流傳了兩千多年的《莊子》讀解難以真正推進。
"內七篇"的第三篇為《養生主》,是"身心兼養的'人生'論",文首提及的"庖丁解牛"即出自其中。作者認為,"第一寓言'庖丁解牛',是'全生寓言'。奧義藏于'善'及'道/技'之辨。"其隱喻了養生"三義":
其一,"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意為"養生"必先因循內德,自適其適。
其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意為進一步"為知"順應天道,當行則行。
其三,"視為止,行為遲",意為落實于"為行"因應外境,當止則止。
可以肯定的是,此處提及的"養生"與當前流行的"養生"是有差別的,此處之"養生"強調"身心兼養,同時以心為主"。該寓言中,庖丁又提到了"良庖""族庖"及自己的三種境界:大知"良庖"一年更換一次刀,因為其以刀割肉;小知"族庖"則以刀砍斫骨頭,因而一月一換刀;而庖丁自己,其刀已用了十九年都還像剛剛在磨刀石上磨過一樣。文惠君最後道出本篇點題語:"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作者認為,"得養生焉"為"養生之主焉"的省略。"養生之主",即"道"也。在作者看來,本篇"形象闡明了保身需技,葆德需道;唯有知行合一,方能身心兼養。庖丁上知真諦,下行俗諦;二諦圓融,覺得圓滿。所'為'被譽為'善',又能'無近名',因而得以'全生'"。
"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全生"是《養生主》一文所闡明的"養生"四境的第二重境界,其余三境為"保身""養親""盡年"。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諸侯連年征戰不息;他身處的宋國,又暴君當道。在亂世中欲保全自身,只有不與力之強者觸碰,避而遠之,如庖丁所說的"以無厚入有間",不與其相割、相斫,故而能"保身",能"全身"。這一觀點,與魯洪生先生對"庖丁解牛"的理解甚為契合。
作者在他的"莊學大廈"的構建中所做的工作,既要透過重重迷霧,將郭象以卑劣手段篡改的《莊子》原文近真復原,恢復《莊子》文本的本來面目,又要將郭象以系統反注而遮蔽了的莊子本來的思想闡發,撥云見日,使莊子思想透過重重迷霧得以再見天日。在《莊子奧義》一書中,作者憑借其強大的邏輯思維能力和史料運用能力,通過文本細讀,深入淺出地闡發了《莊子》"內七篇"深藏的"義理",系統而自洽地找到了莊子所設定的解讀坐標點。這樣的解讀當然是有效的,盡管它並不是唯一的。
有人云:"讀書就是先讀厚,再讀薄",形象地說明了理解與總結的過程,所謂"讀厚",就是逐字逐句掃清障礙,追尋其邏輯演進,理解原文;"讀薄",就是在理解的基礎上去粗取精,提煉書中的核心思想。"讀薄"不易,但對于《莊子》這部文學性充盈的書,"先讀厚"更不容易。其中的每一字、每一詞、每一句,每一處"重言",多隱含"微言大義",需要以全書之大旨進行導引才能准確理解;但是,全書大旨又是在對字、詞、句、段、篇這些進行清晰理解的基礎上才可能深刻理解的。這是一個悖論,但也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閱讀過程。《莊子奧義》一書,既是作者幾十年閱讀《莊子》的心得凝聚,更是多數人真正走進《莊子》之津梁。"得魚而忘筌",若借助于該書真正進入莊子精神的廣闊天地,對于讀者而言,最終"忘其筌"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