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7.15)是俄國作家、劇作家契訶夫逝世的日子。他一生創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說。那些對人性的、市民的、社會的庖丁解牛式的描寫,有種惡毒的幽默感。納博科夫評價契訶夫的幽默:如果你看不到它的可笑,你也就感受不到它的可悲,因為可笑與可悲是渾然一體的。
本文作者童道明先生是研究契訶夫的專家,他一生摯愛契訶夫,他的身上,也散發着契訶夫式的溫和、浪漫、深沉與悲憫。對于童先生,最快樂的事莫過于有人對他說,“我喜歡契訶夫”。

契訶夫的小說創作(節選)
文 | 童道明
契訶夫有句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姐妹。”這句話出自他1889年4月11日寫給他哥哥亞歷山大的一封信。而在三天前的4月8日,契訶夫在給蘇沃林的信中,發表了同樣的觀點:“學着寫得有才氣,就是寫得很簡潔。”
有個實際的事例可以說明契訶夫對于簡潔的追求。
1886年契訶夫寫了篇小說《玫瑰色的襪子》。小說主人公索莫夫娶了個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婆,但他並不介意。“怎麼的?”索莫夫想,“想着談談學問上的事兒,我就去找納塔麗婭·安德烈耶芙娜……很簡單。”但《花絮》主編列依金發表這篇小說時,自作主張在小說結尾處加了一句:“不的,我不去,關于學問上的事兒,我可以跟男人們聊聊。他做了最後的決定。”盡管列依金是契訶夫的恩师,但契訶夫還是用幽默的口吻寫信去表示了異議:“您加長了《玫瑰色的襪子》的結尾,我不反對因為多了一個句子而多得八戈比稿酬,但我以為,這里與男人不相干……這里說的僅僅是女人的事……”
契訶夫惜字如金,他的小說不少是開門見山的。
像《胖子與瘦子》(1883)——“在尼古拉葉夫斯基鐵路的一個火車站上,有兩個朋友,一個是胖子,一個是瘦子,碰見了。”
像《牽小狗的女人》(1899)——“聽說,海邊堤岸上出現了一張新面孔——一個牽小狗的女人。”
《牽小狗的女人》是契訶夫的一個少有的寫愛情的小說,但小說里見不到一點男女主人公之間的肌膚相親的場面,契訶夫只是告訴我們:“只是到了現在,當他頭已經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愛上了一個人。”然後就是寫兩個人分手之後的長相思,也寫到了幽會(但沒有用筆墨去描摹幽會的浪漫場面),而小說的結尾一句也是能讓讀者與兩個相愛着的男女主人公一起“陷入遐想”的:
“似乎再過一會兒,就會找到辦法了,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開始了。但他們兩人心里都清楚:距離幸福的目的地還很遙遠,最復雜和困難的路程才剛剛開始。”
說契訶夫式的“簡潔”,我還想拿小說《阿紐塔》(1886)作例。阿紐塔是學生公寓里的一個女佣,二十五歲光景,她服侍的對象是個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克留契科夫,她唯命是從地聽從這位大學生的使喚,還“與他同居”。這天,克留契科夫已經動了將要辭退阿紐塔的念頭,說:“你要知道,我們早晚要分手的。”而在這之前,契訶夫只用了短短的一段文字交代了阿紐塔的生活“前史”:
“在這六七年間,她輾轉在這些公寓房子里,像克留契科夫這樣的大學生,她已經交往過五個。現在他們都已大學畢業,走上了人世間,當然,他們也像所有的有身份的人一樣,早就忘記了她。”
我讀到這里,心里升起了莫名的惆悵,同時也被契訶夫的簡潔的筆法所感染。我由眼前的克留契科夫而想象到了阿紐塔之前侍候過的五個大學生的面影,又由那五個大學生的行狀而想到克留契科夫“走上了人世間”後也會把阿紐塔忘得一干二淨。
還在莫斯科大學醫學系念書的時候,契訶夫就開始文學創作,那時他都往幽默刊物投稿,而且署的都是筆名,用得最多的筆名是安東沙·契洪特,所以也有學者把這契訶夫初登文壇的時期稱為“安東沙·契洪特時期”。而且研究者們都傾向于把《一個官員之死》(1883)、《胖子與瘦子》(1883)、《變色龍》(1885)、《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等視為眾多幽默小說中的杰作。
契訶夫是懷着什麼樣的人文精神與道德訴求踏上文壇的呢?這可以從他的兩封書信中看出端倪。
1879年4月6日,契訶夫給弟弟米沙寫信說:“弟弟,不是所有的米沙都是一個樣子的。你知道應該在什麼場合承認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尊嚴。”
1889年1月7日,契訶夫寫信給蘇沃林說:“您寫寫他吧,寫寫這個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擠出去的。”
一個小小“文官”在一位將軍面前的恐懼;一個“瘦子”在一個“胖子”面前的諂媚;一個“警官”在一只可能是將軍家的“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一個“一看見有人犯上就冒火”的“中士”,都丟掉了“人的尊嚴”,暴露了“身上的奴性”。契訶夫通過對于人身上的“奴性”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張揚的正是維護人的尊嚴的人文主義精神。
除了“奴性”外,契訶夫還發現另一種人性的扭曲,那就是普通人不甘于當普通人的浮躁。因此,我以為在《一個官員之死》之前發表的《欣喜》(《喜事》,1883),也是值得一讀的契訶夫早期創作中的佳作。
這個幽默作品寫一個十四品文官是怎樣因為在報紙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欣喜欲狂的——“現在全俄羅斯都知道我了!我名揚全國了!”
而這位官職低得不能再低的文官是因為什麼才名字上報的呢?原來是因為他是一樁交通事故的當事人而名字上了報紙的社會新聞!
後來契訶夫在小說《燈火》(1888)里,也通過一個細節描寫,對“小人物”不甘心當“小人物”的“小人物心理”做了令人憫笑的展示——“……還有一個叫克羅斯的人,想必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吧,他是多麼深切地意識到了自己的渺小, 以至于使出狠勁,將自己的名字用小刀往公園亭子欄杆上刻進去一寸深。”——這是俄羅斯式的“XXX到此一游”。
這就是為什麼高爾基能從契訶夫的這些幽默小品中,“聽到他因為對那些不知道尊重自己人格的人的憐憫而發出的無望的歎息”。
“契訶夫小說選”的選家一般都不會漏掉《一個官員之死》等幽默小品名篇,我想除了它們的幽默品質、思想力度外,也因為它們可稱契訶夫的簡潔文筆的典范。
舉知名度最高的《一個官員之死》作例。
在所有的幽默小品中,《一個官員之死》是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打噴嚏總歸不犯禁的”,但這個名叫切爾維亞科夫的小官,“在一個美好的傍晚”去看戲,因為打了個噴嚏,而惹了大麻煩。因為他懷疑唾沫星子可能噴到了坐在他前面的文職將軍的身上,于是前後五次陪着小心,惶惶不安地向將軍做出解釋,賠禮道歉,而被這個小庶務官的反復賠罪搞得不耐煩的文職將軍,終于鐵青了臉向他大吼一聲“滾出去!”而小官員聽了這一聲“滾出去”之後,“肚子里似乎有什麼東西掉下去了。他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退到門口,走出去,慢騰騰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沒脫掉制服,往長沙發上一躺,就此……死了”。
小說的結尾一點都不拖泥带水,卻凸顯了這個小官員之死的荒誕意味。
此外,契訶夫並沒有在這個小官員的外部形態上花費筆墨,他的膽小怕事的人物性格與心理狀態,也是通過人物本身的性格化的動作與言語加以展示的。
1886年,契訶夫寫了一個像童話一樣美麗的小說《玩笑》。那個名叫納嘉的少女,為了能再次在風中聽到“納嘉,我愛你”這聲神秘的呼喚,冒死從山頂向深淵滑去的少女,真是水靈得可愛。《玩笑》和1888年的《美女》說明契訶夫開始用心抒寫女性之美了。
1886年最重要的作品無疑是《苦惱》。
《苦惱》的題辭引自《舊約全書》:“我拿我的煩惱向誰訴說?……”這篇小說的情節很簡單:剛剛死去了兒子的馬車夫姚納,想把他的喪子之痛講給別人聽,但沒有一個人願意聽他的訴說,最後,這位馬車夫不得已,只好把他內心的痛苦講給小母馬聽。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
小母馬嚼着干草,聽着,聞聞主人的手……
姚納講得有了勁,就把心里的話統統講給它聽了……

這個出乎意外的結尾,當然也顯示了契訶夫的幽默才華,但這個含有眼淚的幽默已經與他早期創作的供人解頤的幽默不可同日而語了。
然而,《苦惱》的價值主要還不是在于它表現了馬車夫姚納的苦惱,而是在于通過無人願意傾聽姚納的苦惱這一事實,昭示了一個最令人苦惱的人間悲哀,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是20世紀文學的一個主題。而19世紀的契訶夫已經在自己的作品中觸及了這個現代文學的主題。所以我們可以同意這樣一個觀點,契訶夫生活在19世紀,但他的思想屬于20世紀。
自《苦惱》開端的表現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的題旨,後來在契訶夫的作品中一再重復,成了成熟的契訶夫創作的一個潛在的主題。
而且這個主題是不斷深化着的。如果說,在《苦惱》中,我們看到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還來自人不肯與別人進行交流(別人不願意聽馬車夫姚納訴說他的喪子之痛),那到了後來,契訶夫想告訴我們:即便是存在着交流,甚至在充分的交流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還是存在隔膜,互相無法在心靈上溝通起來。
1886年,契訶夫也寫有一篇幽默小說《一件藝術品》,在這個精致的小品中,契訶夫也用幽默的手法,展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
而契訶夫也正因為他的這種對于人生困頓的洞察力,使他的創作更具有時代精神。
因此,我們可以贊同德·斯·米爾斯基在《俄國文學史》中發表的一個觀點:“在表現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隔膜和難以相互理解這一點上,無一位作家勝過契訶夫。”
契訶夫1887年寫的小說里,《信》值得拿出來專門說一說。
《信》得到過柴可夫斯基的激賞。這位作曲家讀過《信》後給他弟弟寫信說:“契訶夫在《新時報》上登的那篇小說昨天完全把我征服了。他果真是個大天才吧?”
這篇小說是圍繞着一封“信”展開的。執事留彼莫夫的兒子彼得魯希卡在外邊上大學,有行為不檢點的過失,執事便去央求修道院長寫封信去教訓教訓兒子。修道院長寫了封言辭十分嚴厲的信。神父看過信後勸執事別把這封信寄走,說“要是連自己的親爹都不能原諒他,誰還會原諒他呢?”經神父這麼一勸,執事開始思念兒子,“他盡想好的、溫暖的、動人的……”最後便在修道院長寫的“信後面添了幾句自己的話”,而“這點附言完全破壞了那封嚴厲的信”。
契訶夫用靈動的筆觸,把執事留彼莫夫的心理活動及深藏在心里的父愛描寫得既真實又生動。
“書信”也每每出現在契訶夫的其他一些小說里。試看小說名篇《萬卡》(1886):九歲的萬卡在一個鞋鋪當學徒,備受店主欺凌,便給鄉下的爺爺寫信求救:“親愛的爺爺,發發慈悲带我回家,我再也忍受不了啦!”但萬卡在信封上寫了“寄交鄉下的祖父收”,是一封注定無法投遞的死信。這讓讀者讀後愴然有感,知道在契訶夫的幽默里是閃動着淚光的。
《第六病室》(1892)也是契訶夫的一篇小說代表作。“書信”是在小說尾聲出現的。此刻,拉京醫生已經處于瀕死狀態——“隨後一個農婦向他伸過手來,手里捏着一封掛號信……”
這封沒有展讀的神秘的掛號信的內容,想必也應該和正直的拉京醫生的思想相吻合的吧。
拉京醫生在小說里發表了不少激憤的言辭,最讓人動容的是這一句:“您(指無端被關在‘第六病室’的智者伊凡·德米特里奇)是個有思想、愛思考的人。在隨便什麼環境里,您都能在自己的內心找到平靜。那種極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種對人間無謂紛擾的十足蔑視——這是兩種幸福,此外人類還從來沒有領略過比這更高的幸福呢。”
19世紀俄國文壇有兩大奇觀——托爾斯泰的日記和契訶夫的書信。
契訶夫留下了四千多件信札,佔了他全部文學遺產的三分之一。在契訶夫的書信里有他的真心情和大智慧。
在柴可夫斯基喜歡的契訶夫的小說中,還有同樣是發表于1887年的《幸福》。這篇小說寫兩個牧羊人(一個年老的一個年輕的)和一個管家在一個草原之夜的幻想——對于幸福的幻想。而在契訶夫的描寫中,草原上的天籟之音成了詩一般的交響:
“在朦朧的、凝固似的空氣中,飄蕩着單調的音響,這是草原之夜的常態。蟋蟀不停地發出唧唧聲,鵪鶉在鳴叫,離羊群一里開外的山谷里,流着溪水,長着柳樹,年輕的夜鶯在無精打采地啼囀。”
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另一位俄羅斯大作曲家拉赫瑪尼諾夫(1875—1943),也是契訶夫作品的崇拜者,他的研究者說,最讓這位作曲家傾倒的,是“美妙的契訶夫的音樂性”。
最早指出契訶夫作品的音樂性的,是俄羅斯戲劇家梅耶荷德,他曾稱契訶夫的劇本《櫻桃園》“像柴可夫斯基交響樂”。
當然,音樂性不僅來自聲響,同樣也來自張弛有致的節奏,甚至來自有意味的無聲的交響。請看《幸福》是如何結尾的:
“老人和山卡(即兩個一老一少的牧羊人——引者)各自拄着牧杖,立在羊群兩端,一動也不動,像是苦行僧在禱告。他們聚精會神地思索着。他們不再留意對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里。那些羊也在思索……”

注:①指基督教的習俗:聖誕節前夜小孩們舉着用簿紙糊的星星走來走去。
本文節選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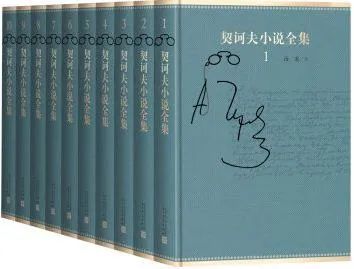
《契訶夫小說全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