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常覺得焦慮在生活中無孔不入:大到人生規划、工作競爭、婚姻生活,小到選擇困難與社交困難......凡此種種,它們带來的焦慮無不拉扯着現代人本就脆弱的神經。那麼你是如何面對焦慮的?逃避抑或是慣性麻木?但這都不應該作為我們正確對待焦慮的方式。
如果你不想再頻繁用着“我太難了”的表情包,沉溺在無止境的焦慮中。你應該直面自己的焦慮、認真審視它,並層層剖析內心深處的恐懼。畢竟,戰勝焦慮的最好方法就是面對焦慮。
本文節選了精神分析學家卡倫·霍妮在《我們時代的精神症人格》中對焦慮的深入分析,或許你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症結所在。

卡倫·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
德裔美國精神分析學家。被公認為是與阿德勒、榮格、蘭克、弗洛姆等齊名的西方當代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主要代表。
恐懼與焦慮
若是一位母親,僅僅因為孩子患上輕微感冒或是身上出了丘疹,就害怕會因此永遠失去他們,我們把這種情緒反應叫做焦慮;但若是孩子患上了重病,她因此而害怕痛失至親,我們則稱之為恐懼。又比如,若是有一個人身處高位,或明明與他人討論的是自己擅長的話題,卻還是感到害怕,我們稱這種反應為焦慮;但若是一個人在電閃雷鳴的雨天迷失於深山老林之中,我們則把他這個時候的害怕稱為恐懼。我們可以將二者作一個簡明的區分:恐懼是在面對危險時恰如其分的反應,而焦慮則是面對危險時不適當的反應,或者可以說其為面對假想危險的一種反應。
無論恐懼還是焦慮,都是對危險的恰當反應。但導致恐懼的危險更明顯且更客觀,導致焦慮的危險則往往是潛在且主觀的。也就是說,焦慮的強弱與當下情景對人的影響成正比,至於其焦慮的原因,表現者自己本人基本上也不知道。
焦慮與恐懼間的這種差異,其現實意義在於讓我們明白,焦慮並不是由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危險引起的,而是由內心感受到的危險所造成。
一般人很少會留意焦慮在其生活中的比重。通常情況下,人們只能回憶起他們童年時有過一些焦慮,或是曾做過一兩個令他感到焦慮的夢,又或是身處日常生活之外的某些境況中曾有過一些擔憂,例如,與一位大人物作重要談話之前,或是一場考試之前。
表現焦慮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
它可能以一種彌散性焦慮的方式表現出來,顯示出焦慮症的發作;也可能依附於某種特定的情境或活動,例如高樓、街道或公共場合;還可以通過更確定的事情表現出來,例如擔心精神失常、患上癌症,或懷疑自己誤吞了什麼異物等等。我們也很可能在承受焦慮時,自己沒有絲毫察覺。
事實上,我們似乎在竭盡全力擺脫焦慮或是避免感知焦慮。這種做法有許多理由,其中最常見的一種便是:嚴重的焦慮是最折磨人的情緒之一。那些承受過重度焦慮的患者可以告訴你其中的恐怖,那是一段寧死也不願再經歷一次痛苦。除此之外,焦慮中包含的某些情感因素,很可能也是個人所無法承受的。
其中一種便是無力感。
面對極大的危險時,一個人仍可以生機勃勃、斗志昂揚,但若是處於焦慮的狀態下,那他只有孤立無助的感覺。對那些把權力、地位、掌控傾向置於首位的人而言,承認自己無能為力是一件絕對無法容忍的事情。他們憎惡這種感覺,因為自己無能為力的現狀與理想中的自己極不相稱,好像那樣就證實了他們的軟弱和膽怯。
包含在焦慮中的另一種情感是顯而易見的非理性。
對於某些人來說,允許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簡直是一件不堪忍受的事情。這些人心中會隱隱覺得自己正處於會被一股非理性的異己力量吞噬的危險境地中,由於堅信理性的力量,他們已經在無意識中將自己訓練成了嚴格服從理智支配的人,因此對這群人而言,他們堅決無法自覺接納非理性因素。除了種種個人動機外,後者的反應行為還涉及到文化因素,因為我們的文化總是極力推崇理性思考、理智行為,對於那些非理性或類似非理性的東西,我們將其一律認作低級之物。
再沒有比意識到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某些態度更令人反感的事情了。然而,一旦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正陷於恐懼與防禦機制的迷網中,他越是束手無策,就越是沉溺於自己將每件事都處理得完美無缺這一錯覺中,進而越本能地排斥任何暗示——即便是間接的或含蓄的暗示。他們不認為自己身上有任何錯處,也不認為自己作出需要任何改變。
在目前的文化環境下,主要有四種掩蓋焦慮的方式:
一、將焦慮合理化;
二、否認焦慮;
三、麻醉自己;
四、遠離一切可能引起焦慮的思想、感情、沖動以及處境。
第一種方式——將焦慮合理化,是逃避責任的最佳解釋:它將焦慮轉化為合理的恐懼,借此達到逃避責任的目的。
如果我們忽視了這種轉變的心理價值,那麼也許就會認為這種轉變沒有带來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就像一位關心過度的母親無論是承認自己焦慮,還是把自己的焦慮解釋為一種合理的恐懼,實際上只是因為擔心自己的子女。然而,我們可以以無數次的實驗結果向這位母親證明,她的反應不是合理的恐懼而純粹是焦慮,並暗示她,這種焦慮是由於她片面地看待危險而最終造成的,其中包含了諸多個人因素。我相信在聽了這話後,她一定會大加反駁,並想盡辦法讓你明白是你錯了:瑪麗小時候不就得過這種傳染病嗎?約尼不就是因為上次爬樹而摔斷腿嗎?最近不是有個人經常用糖果拐騙孩子嗎?她的這些行為不就是因為太愛孩子,害怕他們受傷嗎?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們見到有人為了自己的非理性態度激烈辯護,那就可以肯定,對於這個人來說,這種辯護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那位母親情緒如此強烈,但她不僅不會因為這種情緒而感到無能為力,反而會覺得在這種處境下應該積極做些什麼;她不僅不會承認自己的懦弱,反而為自己的高標准而感到自豪;她不僅不會認為自己的這種態度是由非理性因素引起,反而會覺得自己又理性、又合理;她不僅看不到這種改變自己的挑戰,反而會堅決地將自己的責任轉移給外部環境,並借此逃避面對她自己的內心動機。當然,她最終會為這些暫時的逃避付出沉重的代價,然後永遠也無法擺脫內心的憂慮。更重要的是,她的孩子也會因此付出代價。可她全然意識不到,事實上,她也根本不想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在其內心深處,她始終抱有這樣一種幻想,以為可以在不改變自己態度的情況下得到改變態度後带來的益處。
這一原理適用於所有將焦慮看作是正當恐懼的傾向,無論是對分娩的恐懼,還是對疾病的恐懼,或是對飲食失調的恐懼,甚至是對天災人禍和對貧窮的恐懼。
第二種掩蓋焦慮的方法是否認焦慮本身的存在。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否認其存在,我們並沒有辦法真正地化解焦慮;而否認焦慮的存在,也就是指從意識層面將焦慮排斥在外。
在這一情況下,隨之而來的是恐懼或焦慮的生理反應,如顫抖、流汗、心跳加速、窒息、尿頻、腹瀉、嘔吐等。在精神方面則會有焦躁不安、易衝動或有麻木呆滯的感覺。我們感到害怕,並意識到自己害怕時,以上這些感覺和生理反應便會在我們身上表現出來。同樣,現存的焦慮被抑制後,這些感覺和生理反應也是其唯一的表現方式。在後一種情況下,焦慮的個體能意識到的只有這些外在的表現依據,比如在某些情況下,他總是忍不住要頻繁小便,或在火車上總是覺得頭暈目眩想要嘔吐,又或是夜裏時常盜汗等等。而這些所有的表現,通常是沒有任何生理原因的。
但我們同樣可以在意識到焦慮後,主動選擇否認其存在,換句話說,就是企圖戰勝焦慮。這種情況與一般發生在正常人身上的差不多,就像是故意忽略恐懼一般,逃避它的存在。眾所周知的一個例子就是,一個士兵面對恐懼時,受戰勝恐懼的衝動驅使,他會表現得英勇無畏。
第三種掩蓋焦慮的方式是麻醉自己。這種行為可能是有意為之,可以通過如同“麻醉”表面意思般用酒精和藥物達到目的。
當然,除此之外,也可以采取許多相互之間沒有任何關聯的方式達成。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在處於對孤獨的恐懼下,積極投身到社會活動中去。無論神經症患者是自己意識到了這種恐懼,還是隱隱察覺出了一些不安,這種方式都不可能真正改變神經症患者的處境。另一種麻醉自己來擺脫焦慮的方式,是寄情於工作,這一點可以從一些患者工作上的強迫性傾向,以及節假日休息時的焦躁不安感中窺見一二。
除此之外,盡管過量睡眠往往並不能更好地消除疲勞,但神經症患者也可以通過無節制的睡眠來達到同樣的麻醉目的。最後,性行為也可能被當作是舒緩焦慮的“安全閥”。人們很早就發現,焦慮會導致強迫性手淫,但人們並未意識到,事實上焦慮可以引起各種形式的性關係。對於那群將性行為作為舒緩焦慮的主要方式的人而言,如果沒有得到性滿足,哪怕只是片刻沒有得到滿足,他們都會變得極度焦躁而不安。
第四種擺脫焦慮的方式是所有方式中最徹底的一種,即避免一切可能引起焦慮的情況、思想及感受。
這可以是一段自覺的選擇過程,就像怕水的人避免潛水,怕高的人不願登山一樣。說得更准確一點就是,一個人可以自覺地意識到焦慮的存在,並且有意識地避免它。但他也可能只是模糊地感覺到其存在,模糊地意識到自己逃避焦慮的方式,或是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受焦慮的折磨,也根本意識不到自己選擇的逃避焦慮的方式。例如,他會在絲毫沒有意識的情況下,用拖延事情進度的方式逃避那些與焦慮有關的事情,比如遲遲不做決定、拖着不去看醫生或一直不回信等等。或者,他可以“假裝”無所謂,即主觀地認為那些實際上他極為在意的事情毫不重要,例如參加討論、對雇員發號施令、與他人斷絕關係等等。又或者,他可以“假裝”自己不喜歡做某些事情來達到擺脫焦慮的目的。例如一個女孩,因為害怕在晚宴上受到冷落而拒絕參加晚會,並想方設法讓自己相信,這是因為自己本來就不喜歡社交集會。
逃避產生的抑制狀態
如果我們再深入一步,去探求這種逃避傾向在何種情況下會自動發生,那麼我們就會遇見一種抑制狀態。這種抑制狀態的表現為:無法完成正常的事情、無法感受情感或無法思考問題,而其作用就是避免因這些事而引起的焦慮。在這種狀態下,患者無法自覺意識到焦慮,也就無法通過自覺的努力來克服這種抑制狀態。這種抑制狀態在癔症型功能喪失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例如,癔症型失明、癔症型失語或癔症型肢體癱瘓等等。在性領域中,抑制狀態通常表現為性冷淡及陽痿,但不可否認,這些性抑制的結構可能非常複雜。在精神領域中,抑制狀態又表現為難以集中注意力、難以形成或表達自己意見、不願與他人接觸等等,這些都是人們所熟知的抑制現象。
現如今,抑制作用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現象,而且,一旦抑制作用充分展現出來,是很容易被人辨識的。盡管如此,對於那些帮助我們意識到抑制存在的先決條件,我們仍需簡單地思考一下。否則,我們很容易就會低估抑制作用發生的頻率,要知道,在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意識不到自己身上究竟發生了多少抑制作用。
首先,我們必須先意識到對做某件事的渴望,然後才能意識到對這件事而言自己的能力不夠。舉例來說,我們只有先意識到自己對什麼有野心,才能意識到我們在那方面有哪些抑制。可能有人會問,我自己的願望我自己難道不知道嗎?
事實上,我們的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讓我們設想這樣一個情景:一個人正在聽另一個人讀文章並同時進行思考,聽着聽着,他發現自己的意見與文章中的相左。這個時候,如果他身上的抑制作用很微弱,他便會萌生怯意,不敢將自己的批評意見表達出來,但若是其身上的抑制作用很強烈,這種抑制就會阻礙其組織自己的思想,很可能在討論會結束後,或者第二天清晨,他才能組織好自己的想法。這種情況下的抑制作用只會延緩個人思想的形成,但若是抑制作用變得更加強烈,甚至也可以令人根本無法形成任何批評意見。若是出現了這種情況,假設他確實不同意文章中的觀點,也可能會盲目接受別人所說的一切,甚至還表現得十分贊賞這種觀點。換句話說,如果某種抑制作用足夠強烈,強烈到會阻礙我們的願望及衝動的地步,那麼我們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識得到這種抑制作用的存在了。
因此,實際上,每個人都給自己建立了我之前提到過的防禦機制。一個人越是病態,防禦機制對他人格的影響就越大,他無法去做或者想不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盡管根據他的生命力、精神狀態或教育背景,讓我們可能對他抱有期待,希望他可以完成這些事情,但結果也總是令人失望的。焦慮越是嚴重,表現出的或微妙或明顯的抑制傾向也就越多。
本文節選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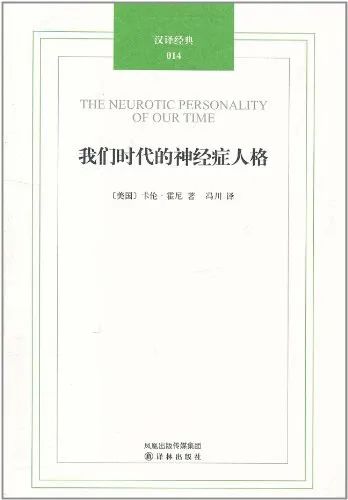
書名:我們時代的精神症人格
作者: [美] 卡倫·霍尼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譯者: 馮川
出版年: 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