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為何總是期待“寒門出貴子”?
[摘要]人們之所以對“寒門出貴子”敏感,出于對教育促進“社會流動”功能的期許和想象,飽含教育與考試讓每個人實現躍遷機會均等的期待,具體到奮斗過程中,希望包括何江在內的勵志故事具有普遍性。

毛坦廠中學萬人送考
作者 潭口蠻
6月7日是高考的第一天,此前,媒體早已開始一年一度的新聞大戰。高考工廠毛坦廠中學是個出大新聞的地方,6月5日,該校萬人送考圖爆紅網絡,可以預料,高考結束後,媒體又將對狀元故事深度解讀。
高考早已不是新聞,但之所以年復一年地吸引眾人眼球,它的魔力在于考試寄托了公眾對于社會流動的期待,特別是“寒門出貴子”,更能制造話題。前不久哈佛大學畢業演講首位大陸生何江能成為國內網紅,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媒體對其“寒門”背景的報道。
不過,何江認為報道屬于過分解讀。問題是,我們為何會對“寒門出貴子”的新聞如此敏感?
一、古代科舉造成社會流動的想象,使人相信寒門能出貴子
對“寒門出貴子”的敏感,體現出我們對“社會流動”的期待和焦慮。在別人一本正經、高談闊論教育可以教書育人、淨化心靈和包治各種疑難雜症的時候,我們心底回響的是高三班主任的諄諄教誨:“出人頭地靠讀書”、“屌絲逆襲要讀書”。面對各種旁征博引、氣勢恢宏的讀書無用論,學區房的價格仍然“蹭蹭蹭”地往上飆。可見,一萬句“無用”論,都比不上宋真宗趙恒的一句“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說起寒門與貴子,很多人會聯想起古代的科舉制度。古代讀書人從“田舍郎”到“登天子堂”的驚險一躍,靠的就是科舉制度。事實上,科舉制度,的確為社會底層開辟了向上流通的渠道。余英時在《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中提到:科舉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制度,它一直在發揮着無形的統合功能。從上層來看,王朝通過“開科取士”把最具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識技能的讀書人選拔進行政系統。從底層來看,科舉為底層社會群體實現持續地向上流動提供了一種制度的可能。通過對明清時期4萬個進士和舉貢的家庭背景進行分析,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中指出這些人祖上三代都沒有功名的比例高達40%以上。因此,明清時期中國的社會流動性遠高于同時期的西方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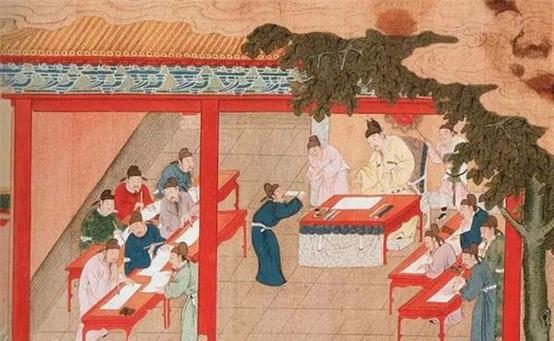
古代科舉殿試圖
以當今社會作考察,77、78級大學生不但是從千軍萬馬中沖出來的少數佼佼者,而且在政壇、學界都有很大影響。恢復高考以來,無數人通過高考實現了跳出農門、改變命運的理想。不少人在講述自己成功經歷時,除了小時候吃過苦外,還往往強調“教育”的作用。
可以說,人們期待“寒門出貴子”,主要是基于上述經驗與現象的認知。後來隨着平權思想的傳播和“成功學”的泛濫,每一個人都比以往任何時代更渴望從金字塔的底層走到頂端。人們相信通過後天超出常人的勤奮和努力,就可以克服在天賦和家庭等方面的劣勢,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于是,一些古往今來、稀奇古怪與“廢寢忘食”、“刻苦讀書”相關的故事都備受青睞。
人們也借助一些儀式來實現自我暗示,比如,在課桌上刻個“早”字展示有自我約束能力,或是在很多場合背誦座右銘來表明自己有遠大理想。為了體現忘我的境界,達芬奇畫雞蛋、牛頓煮懷表是標配的故事。由于吃墨汁的故事太有戲劇性和寓意性,我們也搞不清到底是陳毅吃糍粑沾墨水,還是王羲之、陳墨子、陳望道、茅以升更喜歡喝墨汁。在讀書無用論不絕于耳、社會固化展現出各種“狠”的背景下,“寒門出貴子”無疑寄予了我們對教育和高考的過多厚望。
二、心態上,文字與知識的“魔力”讓貴子之“貴”備受期待
很長一段時間內,考上清華北大的高中生,在當地所得的禮遇,可比之于近六百年來金榜題名的進士。若考生出身農村,一些老人總會誇他“吃上了國家糧”。雖然現在“天之驕子”的提法不時興,但對知識人的崇拜仍然不減,他們改稱為“學霸”。公眾口味也叼,清華北大“學霸”不稀奇,哈佛學霸才夠格讓公眾膜拜。
這種“貴”氣,不局限于寒門。若带上寒門的標簽,當然更適宜傳播。那麼讀書之“貴”,貴自何來?輿論對初露頭角的“知識分子”為何如此追逐?
還得從國人內心對文字與知識的傳統認知說起。簡單說,在非讀書人眼里,文字和知識有神秘感,被賦予了“魔力”。古人相信文字是“古聖賢心跡”,所以字紙不可穢用,廢棄的字紙,應于焚化。這一傳統,儒釋道三教都重視,寺廟有小冊子教人惜字敬字。《淮南子》中提到蒼頡創造文字的時候,有鬼夜哭。古代祭祀,也通過把祭文寫在紙上而與鬼神相通。道教也認為文字是與鬼神相同的媒介,不管是畫符還是讀科儀請神都依靠了文字的魔力。

人們相信,敬惜字紙,天官就能賜福
文字的象征意義,被廣泛運用。我們相信,在木板上寫字就可以代表祖先的靈位;通過語言的咒罵,可以使一個人倒霉;文字背後附着着精魂,可以治病,可以求福,也可以害人;相信燒掉字上的文字可以與鬼神和逝去的親人進行溝通。美國學者武雅士認為,神和鬼分別是官員和外來危險在人頭腦中的映射。文字的神秘性和“魔力”,在于它在傳統社會中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這些人背後往往擁有權力、法力和與更上層進行交往的能力,毫無疑問,少數人中的多數,就是知識分子。
這種體現在知識分子身上的“魔力”最終體現在社會實際中。電視劇《大地恩情》中,楊九斤文父親回答為什麼要給地主交租,他並不是說土地是地主的,而是說地主是舉人公,舉人公就是天上的文曲星,所以要給他交租,足見“舉人”在他心中的地位。可以說,掌管“文字和知識”的讀書人身份,能夠獲得尊重以及支配社會資源。這就是讀書人之“貴”,人們對文字與知識“魔力”的崇拜,外在表現于對讀書人的崇拜,進而轉化為穩定的文化心理。

清代文曲星木雕。
當然,在教育已經普及的今天,不會再有一個群體能夠壟斷文字和知識,附着在文字和知識背後的“魔力”也在逐漸消退。不過,人們對魔力的渴望仍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毛坦廠中學出征的首車車牌號碼是666,司機要屬馬,儀式設計者就希望借文字的“魔力”討個吉利。一旦該校有了狀元,下一輪就是更高維度的魔力——“知識改變命運”的宣傳與炒作了。
三、期望“寒門”弱者的成功,能打破社會固化的現實
面對社會固化的現實,“寒門出貴子”既是一種道德的訴求,也是在通過他者的成功逆襲來完成自我的安慰,是對未來還充滿一絲好感和期待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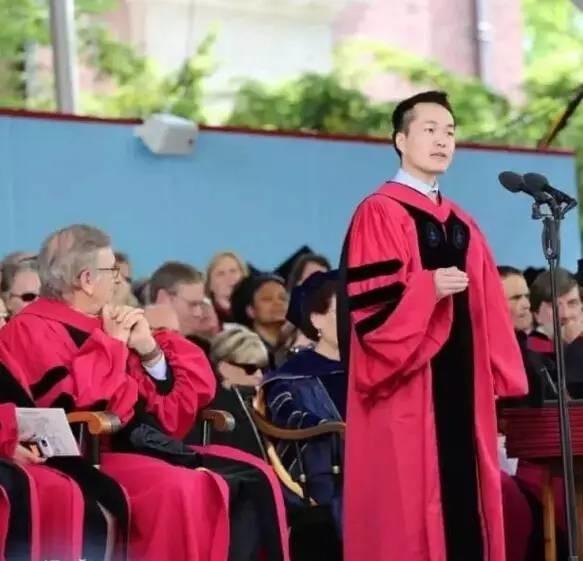
哈佛演講畢業典禮上首位大陸畢業生何江在演講。
從照顧弱者的角度看,“寒門”要比其他人更有資格獲得更好的教育,獲得更多的社會成就。但現實是,現代的高考出題使得教育資源對最後的結果影響權重越來越大。寒門學子勞其筋骨之後,無論你如何苦其心志,也無法戰勝本身佔有優勢教育資源並購買教育的學子。這些人形成“知識壟斷”和“知識壁壘”,進一步阻礙社會流動。
《我奮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之所以被廣泛傳播,是因為它確實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對于“寒門”來說,他的優勢是千金難買的少年志。但現實卻與道德相反,很多家里的背景,不但志氣不小,還比你更熱愛學習,享有更多的教育資源。當“寒門”唯一的優勢都不明顯,甚至還有可能變為劣勢,“寒門”的未來還有什麼指望?人們總是期待成功者是“寒門出貴子”,是希望能夠有人來打破這種現實,讓弱者的道德優勢在現實中得以實現。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中指出:當代資本主義形成了鼓勵權力和財富繼承,並且能夠不斷自我完善的制度,這使得世界的貧富差距不斷加大。出生在什麼家庭是不可改變的,可以改變的是自己的奮斗,並且通過讀書放大這一後天因素的作用。曾國藩說:“人之氣質,由于天生,很難改變,唯讀書則可以變其氣質”,說的是天賦難以改變,唯有靠讀書。在福柯看來,權力制造知識,知識是權力的代言人,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带的。教育通過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從而影響外部的制度環境。作為對弱者的補償,教育能夠放大個人奮斗的效果,對抗繼承的固化作用。即使通過教育實現“寒門出貴子”在現實中越來越難,但保留着這一念想,保留對文字中“魔力”的想象,也是弱者擁有道德優越感和實現自我安慰的重要支撐。
結語
簡單來說,人們之所以對“寒門出貴子”敏感,主要還是出于對教育促進“社會流動”功能的期許和想象,飽含教育與考試讓每個人實現躍遷機會均等的期待。具體到奮斗過程中,人們希望包括何江在內的過往勵志故事具有普遍性,相信只要通過超出一般的付出也可以復制“寒門出貴子”。這些“期待”更應有條件轉化為行動與現實,不應只是普通人的一廂情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