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我一直心懷崇敬,不只因他與英籍夫人戴乃迭合作將《紅樓夢》《離騷》《儒林外史》《老殘游記》《魯迅選集》等上百種中國經典作品翻譯成英文,推向世界,還因他睿智豁達的人生態度和風趣幽默的做人風格。
記得在鳳凰電視台《魯豫有約》訪談中,魯豫問楊先生為何不給愛妻戴乃迭修一座墳墓,好有個紀念。老人遲疑了一下,接着把手里的煙灰往煙灰缸一彈,說:「人死了就像這煙頭變成了一把灰,修再高級的墳墓又有什麼意義呢?想她的時候看看她的照片、讀讀她的文字,就是最好的紀念!」
《漏船載酒憶當年》是楊先生1990年應意大利朋友的要求用英文撰寫的,1992年翻譯成意大利文出版時取名《從富家少爺到党員同志》,那時楊先生77歲。后來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繁體中文版的時候,直戳戳地取名《白虎星照命》。而《漏船載酒憶當年》,則是2001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時的書名。
得知楊先生有這本書已經很晚了,最近收聽鳳凰衛視N年前梁文道的「開卷8分鐘」音頻節目,才知道楊先生29年前就出版了這本自傳。網上欲購時早已脫銷,無奈只好買了個影印本,插圖照片雖然模糊,但字跡還能對付看,於是一口氣讀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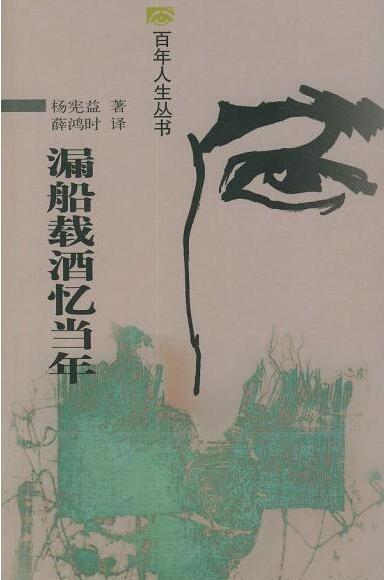
楊先生書中毫不隱諱,開篇就介紹自己的身世。特別有意思的是,他說母親在生他之前得了一夢:夢見一只白虎躍入懷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說,這個夢既是凶兆又是吉兆--這個男孩將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克父傷子,而他在經歷重重磨難后,將會成就輝煌的事業。算命先生一語成讖,他果然是母親唯一的男孩,而且5歲時父親病逝,中年時兒子自殺,自己一生歷盡磨難,最後終成翻譯大家。
楊先生1915年出生在天津巨商之家,爺爺當過江蘇淮安知府,父親是天津中國銀行行長,他是個口含金匙長大的富家少爺。富足的家資,使他從小有條件到天津英國教會學校新學書院讀書,而後又漂洋過海到牛津大學深造。6年的牛津留學,不僅使他學習了古希臘羅馬文學和英國文學,游歷歐洲,開闊了眼界,最後還带回了個漂亮的英國姑娘戴乃迭。

戴乃迭的父親是位英國傳教士,后來一直在中國西北從事教育工作。戴乃迭出生在北京,自幼就對中國、對北京有着濃厚的興趣和情感。1936年,楊憲益在英國牛津留學時倆人相識,不久便成了好朋友。大概正是楊憲益身上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讓戴乃迭愛上了他。后來,戴乃迭乾脆改學中文,成為牛津大學攻讀中文學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趣和事業上的相投,使他們成了彼此的知己,也為日后共同的翻譯工作鋪就了道路。
1940年楊憲益在牛津畢業后,攜戴乃迭輾轉萬里回歸祖國。很難想象像戴乃迭這樣一位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會跟隨楊憲益來到當時正處於戰亂之中的中國。
回國后,楊氏夫婦不斷地在重慶、貴陽幾個城市間教學奔波,直到1943年經友人推薦他們才去了梁實秋領導的國立編譯館。當時的國立編譯館只有西譯中,還沒人做中譯外的工作。梁先生便動員他們夫婦專門去做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從此開啟了倆人的中文外譯事業。

楊先生選擇翻譯的第一個經典是《資治通鑒》。他發現,他和戴乃迭在翻譯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通常是他手捧中國古典名著進行口譯,戴乃迭則雙手在英文打字機上跳動飛舞。
在楊先生看來,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翻譯的,就連中國的《楚辭》也不例外。留學英國留學時,楊先生的文采和聰慧在牛津有口皆碑,當時出於好玩,他一口氣把《離騷》翻譯了出來。譯作充滿了嘲諷與夸張,這一年,他24歲。「我始終認為《離騷》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幾個世紀的漢代淮南王劉安。「他認為,既然原作都是贗品,譯作就更可以天馬行空了。」
1953年,楊憲益跟一群科學家、藝術家一起接受毛澤東的接見。周恩來特別向毛澤東介紹:這是一位翻譯家,已經把《離騷》譯成了英文。毛澤東握了握他的手說:「你覺得《離騷》能夠翻譯嗎,嗯?」楊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主席,諒必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可以翻譯的吧?」毛的反應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頗有幾分不以為然。。
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楊憲益夫婦就應邀來北京到中國外文出版社 (現中國外文局前身)剛剛創立的英文版《中國文學》雜誌工作。這段時間夫婦倆以驚人的速度翻譯了大量中文作品,包括英譯三卷本的《紅樓夢》--這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紅樓夢》。《紅樓夢》英文全譯本的出版,不僅是中國和英語國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學翻譯的大事,它促進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進程。然而,楊先生的妹妹楊苡卻曾聽哥哥說過,他其實並不喜歡《紅樓夢》,他們夫婦倆是把它當成任務硬著頭皮翻譯出來的。
南京剛解放的時候,楊先生的朋友、加拿大駐華使館代辦朗寧,在使館撤離南京前告訴楊先生,他在收拾使館財物時發現一只舊木櫃內藏有紙包的四千多塊上面刻有文字骨片。朗寧認為這是中國的文物不能带出國,就問楊憲益怎麼處理。楊憲益去看了這批文物,認定是殷商甲骨,就叫了輛三輪車直接將這批珍貴的甲骨文送交給了南京博物院。后來這批甲骨文又轉移到了北京。最讓妹妹楊苡感動的,是「文革」后楊先生坐了4年牢出獄時,將一生收藏的200多件書畫文物,全部無償地捐贈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
「文革」開始,楊先生自然在劫難逃。他回憶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誕。他記得當時造反派們批斗兩名領導,除了敲鑼打鼓和轉圈游斗,還隨處張貼大字報。「很顯然,這兩名領導人的主要罪狀就是他們愛吃好東西。大字報上滿載著他們早先吃過的美味佳肴的詳細紀錄。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變成了一家大飯店,到處都張貼起用斗大的字書寫的菜單。」很快,批斗的矛頭就從領導蔓延到了楊憲益這樣的「專家」和「壞分子」頭上。
他說,一次造反派將三張飯桌一張架一張地摞在一起,然後讓他爬到最高處低頭站立,群眾聚合在桌子周圍對他進行批判聲討,質問他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為什麼要為赫魯曉夫辯護。
他說,有時造反派讓他們低著頭在台上站成一列,然後強迫他們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舉過低垂的頭顱。他說,我胳膊的肌肉很靈活,有彈性,所以能輕而易舉地做出這種姿態。而有的人就不行了,翹不多久就歪倒了,我心裏暗自發笑。
他說,有段時間我被勒令打掃廁所……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殘存的陳年污垢統統刮掉,用清水沖乾淨。不久,我就因為工作出色而受到人們夸獎,《中國文學》編輯部的廁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潔的廁所。
后來,楊先生開始出現輕微的神經分裂征兆,他常有幻聽,並產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臨的是孤獨與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與這個金色頭發的外國女人說話,她走到哪裏都會碰到敵意的眼神,人們像躲避瘟疫一樣地躲著她,有些激進的學生甚至當著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英國佬!」
戴乃迭所在單位的領導質問過她:你為什麼不加入中國國籍?戴說:「只有加入中國籍才叫愛中國嗎?你是什麼共產党員?一點國際主義思想都沒有!」說得對方啞口無言。
1968年4月,美籍猶太人愛潑斯坦和他的英國籍妻子被捕入獄。不到一個月,就輪到了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楊先生被捕那天,夫妻倆正在家中對酒澆愁。楊先生入獄時滿身酒氣,同獄的犯人以為他是因為喝酒鬧事才被抓的,他吸著鼻子說:「你的酒氣好聞極了,一定是高檔貨,多少錢一兩的?」
楊先生告訴他,他買的酒不是散稱的,是論瓶的。離家的時候,他跟太太剛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還留著三分之一。這讓同監的獄友垂涎不已。
楊憲益在獄友中很快贏得了尊敬,與此同時,戴乃迭被關在另一所女子監獄里。他們最放心不下的是三個孩子,但監獄的看守告訴他們,孩子有人照顧。戴乃迭出獄后才知道:她的三個孩子,幾年內沒有一分錢生活來源,衣食無著,流落在農村。
郁達夫的侄女郁風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橋監獄。郁風說,在獄中,這位可敬的英國女子也依然保持著文明的風度,她愛清潔,用牙刷把監獄的牆刷得干乾淨淨,每天送牢飯的過來時,隔著一條走廊的郁風聽見戴乃迭從來不忘記對獄卒說「謝謝」。
獄中的楊憲益依然保持著對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發生,但是監獄里的犯人們對外面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按照慣例,每年國慶節那天,准許犯人從收音機里收聽天安門廣場的慶祝廣播。而這一年,楊先生注意到,林彪沒有照常出來以嘶啞的聲音發表演說,甚至連名字都沒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這一信號,並尋找到了佐證:《人民日報》上刊登的西哈努克親王的賀電只發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兩人,這是極不尋常的。「當時西哈努克親王被認為是中國最親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度過。如果林彪繼續得寵,西哈努克絕不會犯一個如此嚴重的錯誤。」楊憲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紅寶書」,把第一頁林彪寫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后,看守走進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紅寶書」統統交上來。當他拿到楊憲益那本發現林彪的前言不見了時大惑不解,他又翻看了一遍,還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麼話都沒有說,就把那本小紅書扔還給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書都带走了。」這一舉動使所有犯人都覺得奇怪,楊先生卻暗自得意,他告訴獄友,外面可能快要變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楊憲益到一個很大的房間,往他的脖子上掛了一塊寫有名字的紙板,並打開所有的燈,讓一名攝影师進來給他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所有的犯人都一臉憂傷--看來楊憲益要被槍斃了。
但第二天,楊先生被带了出去,一位監獄的官員對他發表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談話,大意是:你干過好事,也干過壞事;當初抓你是對的,放你也是對的;你在監獄呆了4年,伙食費要從你的工資里扣取。說完這一切,他們就讓楊憲益出獄了。
楊憲益出獄后不久,戴乃迭也被無罪釋放了,在政治高壓的年代里,這對異國夫妻所付出的代價無疑是巨大的。在之後的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楊戴夫婦聯袂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到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老殘游記》,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紅樓夢》和《魯迅選集》1-4冊,多達百餘種。戴乃迭的母親曾對她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后悔的。」但戴乃迭沒有后悔,她說:「愛上了中國文化,才嫁給了楊憲益。」

早在楊戴兩人結婚之前,雙方的母親就對這門婚事十分擔憂,乃迭的母親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對,她甚至對女兒說:如果你們結婚,你們的婚姻持續不了4年,而你們將來的孩子會自殺而死。是詛咒還是讖語?楊憲益最疼愛的兒子楊燁,因為「文革「中受到父親的牽連,逐漸神經分裂,在姨媽家中用汽油點火自焚。這成為一生恩愛的楊戴二人之間永恒的隔閡,戴乃迭始終認為楊憲益在兒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不改初衷,堅信對楊憲益和中國的選擇,從未后悔和動搖過,無論戰亂、流亡、貧困……直到兒子的死亡,她開始懷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內心深處,她更因為母親當年的預言應驗而深感挫敗。
「文革」結束后,楊憲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續,他的學術抱負也得以施展,在這段時間里,他除了跟乃迭繼續翻譯作品,還常有機會與友人聚會和旅行,寫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詩作。楊憲益自嘲是:「學成半瓶醋,詩打一缸油。」雖然不少詩歌是含諷的打油詩,但整體看來,這一段時間,楊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的「百萬莊」寓所,出入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經常來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黃苗子、黃永玉、丁聰、新鳳霞、郁風……除了相伴出遊,他們在詩文書畫上也互有酬答。
可以說,楊憲益、戴乃迭以他們事業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結合創造了一個中西文化親密無間、水乳交融的獨特範例。幾十年來,他們珠聯璧合的合作,使他們雙雙獲得了「譯界泰斗」的美譽,他們不僅創造了翻譯史上的奇跡,更用一生成就了一個傳奇。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癡呆症,楊先生與她寸步不離。朋友們去看望她,她有時已認不出他們,但她一直微笑著,白色卷發松軟地圍著老太太泛紅的臉。郁風就這樣為她畫了一幅肖像,他在畫上題了兩行字:「金頭發變銀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會變的。」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楊憲益也停止了翻譯工作。乃迭去世以後,這幅畫就長伴楊先生案頭。他還作了一首詩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發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聯詩的人越來越少了。有人說,楊憲益也許是中國最後一個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識分子了,沒一點兒夸張。
2009年11月23日6時45分,這位中國著名的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文化史學者和詩人在北京煤炭總醫院逝世,享年95歲。
楊先生去世一晃12年了,他接受魯豫訪談時侃侃而談的情景至今還能在腦海中清晰浮現,他的「有煙有酒萬事足,無党無官一身輕」的豁達與瀟灑,更讓我至今難忘;他的親愛的夫人戴乃迭女士也去世22年了,一個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不遠萬里來到當時還是戰亂中的中國,與楊先生甘苦患難幾十年,為傳播中華優秀文化貢獻了畢生。他們二位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作者:王傑,深圳報業集團編審,報紙專欄作家,出版過散文著作《三情集》《鄉愁,抹不掉的記憶》)



